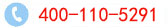课室”的创立及其运用源自亚当·斯密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基于其人性假设和社会制度构想,他认为人的德性和智慧的成长需要教育的力量,主张国家担负普通民众公共教育的责任。为实施其教育蓝图,他设计了系统而严苛的学科规训课程和国家层面的入职考试制度,创制了日常化教学测试,从而彰显权力对一些知识形式和教育实践形态的掌控力量。在教育规训制度下,教室中的考试、评分促使教学双方都面对经常性监视和评判,激发其自我反省自觉,从而不断生成、建构自我审查的主体,同时也改造或重塑其观念世界。
斯密(Adam Smith)在经济学、伦理学界已为人所熟知,但很少有人把他看作教学法上的开拓者。从斯密的大学教学经历入手,追溯当下世界各地通用的教学场所——课室(classroom)的源起,审视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内所实施的学科训练、考核及其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探寻教育规训制度的源流。
一、课室的创立:斯密教育之探索
(一)大学教学之路
从学习和教学经历来说,斯密曾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就读,获得斯内尔奖学金去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深造,毕业后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做了两年讲师,又回到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职位。在爱丁堡大学,他主讲英国文学课,还讲授修辞学,其教学讲义中的修辞学部分富有创意,在听课的法律系学生和青年牧师中引起反响。此外,斯密还讲授经济学,同时他把自由贸易学说作为讲课主题,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已初见端倪。随后斯密离开爱丁堡大学,到格拉斯哥大学任职,这主要缘于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讲座教席空缺,在应聘者中斯密成为最合适的继任者。按照当时苏格兰的大学学科分类法,修辞学和文学属于逻辑学讲座的范围,法学和政治学属于道德哲学讲座的讲授内容[1]41。从授课内容来说,逻辑学讲座内容与斯密在爱丁堡大学的授课内容基本一致。就任职资格而言,一方面斯密在爱丁堡大学教学中展示了丰富的学识和不俗的授课天资,其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卓越表现赢得良好声誉,另一方面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时聪慧好学、成绩优异,深得曾教过他的教授的赏识。这些教授当时是大学评议委员会的成员,在聘任教授的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的推举之下,大学评议会一致表决同意斯密为逻辑学教授。
任逻辑学教授后,斯密最初教学的大部分时间讲授修辞学和文学,这也是他在爱丁堡大学讲授的内容,因而讲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在讲授逻辑学的同时,他还接替因病不能讲课的道德哲学教授的授课任务,主讲道德哲学。在爱丁堡大学,他曾讲授过自然法学和政治学,道德哲学不仅为斯密所熟知,而且是他的志趣所在。早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时,斯密就热衷于自由、劳动和价值等学说的钻研,同时在其老师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教授引领和启迪下,主张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自然法学的一个分支系统。因此,让他讲授道德哲学课程不仅他“非常高兴地接受”,而且也是“他最喜欢教的”[1]41。他兼任道德哲学授课任务时间不久,原来的道德哲学教授病故了,斯密又顺利地转到道德哲学讲座,成为讲座的主持者。有学者认为,斯密选择道德哲学讲座,主要是由于他喜欢讲授道德哲学涉及的科目,此外从经济收入条件看,斯密的这一选择也许与道德哲学教授的薪酬比逻辑学教授薪酬高有关[1]45。
(二)大学管理之责
斯密除了任道德哲学教授外,还兼任学校的其他行政职务。按照苏格兰的大学管理体制,格拉斯哥大学当时存在两个分立的自治体,从而具有两个分立的管理机构:一是大学层面的评议委员会,它由校长、教务长、教授会会长、教授会教授及五位讲座教授组成;另一个是学院层面的教授会,它由十三位教授组成,其中拉丁文学、希腊语、逻辑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讲座教授为礼服教授。这些礼服教授的权力和地位高于非礼服教授,听他们讲课的学生都必须穿大学礼服,以示敬重[1]64。格拉斯哥大学的这种管理体制源自欧洲中世纪原型大学的组织模式,其组织结构实质上是行会组织的翻版[2]。以行会师傅自居的讲座教授享有崇高的地位,拥有教学和学术等事务的决策权。从权力形态上,教授会是教授(师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它掌控学院内部的管理和财政预算。在大学层面上,讲座教授是大学评议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拥有相当大的议事权和决策权。作为道德哲学教授,斯密既是礼服教授又是大学评议委员会和教授会的成员。在十三年教授生涯中,斯密除了承担学术研究和教学任务以外,还兼任“学校的财务主管”达六年之久;他还曾担任教务长职务,全面监督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学位授予,监督大学遵守相关法律[1]6164。1761年他又担任了该大学副校长职务,以副校长的身份主持该大学的校务会议[3]15。由此可见,斯密既是讲座教授,又是身兼数职的大学行政管理者。
(三)教育教学改革
赵昌木:课室的创立与现代教育规训的生成
斯密基于讲座教席和行政管理职责,对大学的教育教学进行改革和探索,尤其在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场所的改革方面有所突破,使格拉斯哥大学成为教育和智力创新中心。在教学计划上,斯密初任逻辑学教授时,大幅度地修改其前任教授所执行的教学计划,打破经院式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禁锢,着力于修辞学和文学的讲授,引导学生钻研和探究更有趣、更本源性的问题。在教学内容方面,斯密授课不囿于某一学科领域,讲课内容常常超越学科边界,展示其渊博的学识和思想力度。据他的学生回忆:“斯密由逻辑学转到道德哲学讲座后,有时也讲授美学和哲学史,并用旧讲义讲授文学”,“在讲解哲学著作时,也以他渊博的学识发表一通议论或举一些生动的实例。……他的议论和实例妙趣横生,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既有深刻的寓意,又有很强的批判性”[1]52。斯密讲课旁征博引,生动有趣,深得学生青睐。为了更好地拓展教学空间,提升教学效率,斯密在讲座教席和副校长职位上,力推教学场所的改革,于1762年5月11日主持召开六人会议。这次会议上,他首先使用英语“课室”(classroom)一词(这是他创用的一个新术语)[4]4,同时他还决定把一个学院的议事厅(chamber)转用作“课室”(classroom)[4]76。
英国学者汉密尔顿(Hamilton David)曾对“课室”(classroom)进行了词源学考察。首先,在其著作《走向学校教育理论》中,他指出,斯密把“class”和“room”组合成一个新词(classroom),其本真涵义是指“上课的房间,科目训练的处所”,且只适合于较少人数的教学。而规模化、容纳人数较多的“教室”(teaching rooms)到19世纪初期才出现[4]10。因此,我们把“classroom”翻译为“课室”更符合斯密的本意及其所处的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经济和教育发展状况[5]。其次,汉密尔顿还发现最早使用“classroom”的是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历史文献中[6],之后逐步传播到其他地方,甚至成为19世纪小学教育中的术语[7]。在他看来,这一新词的创用及其传播与斯密所处的经济、文化和知识中心——格拉斯哥密不可分[4]91。当时的英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格拉斯哥工厂林立,经济发展迅速,贸易往来兴盛,商人云集。格拉斯哥大学学者众多、名人荟萃,如数学家西姆森(Robert Simson),伦理学家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布莱克(Joseph Black),蒸汽机发明家瓦特(James Watt)等人都在格拉斯哥大学讲学或做实验[1]1065。商人在与各地贸易往来中时常发生经济纠纷和摩擦,这些纠纷和摩擦激发着聪明的商人和智慧的学者进行激烈争论。斯密不仅参与各种经济、教育问题的论争,而且还提出自由贸易学说和教育理论设想。这些学说和设想伴随着工业产品的输出而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
二、课室中的理念:亚当·斯密教育之主张
(一)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
斯密先后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其授课讲义涉及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修辞学和文学等学科,构成完整而庞大的学术思想体系。在讲授道德哲学课的同时,他把道德哲学的伦理学部分讲稿内容出版,成为《道德情操论》,后来又在其政治学讲稿内容基础上不断积累资料,著述完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些讲稿或著作对人的本性和道德、社会分工及人的教育等问题进行深入阐释,勾勒出理想的社会制度和教育蓝图。
在两部著作中,斯密探讨了人的本性。他认为人的天性是追求私利,但人能够自发实现道德生活,从而达致财富与德性的完美统一。这种人性假设超越斯密之前的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人性主张。霍布斯认为,在人类的天性中,人为了求利、求安全和荣誉而不惜诉诸于争斗或暴力。为了摆脱相互争斗、恐惧不安的自然状态,人甘愿放弃原享有的自然权利,从而把权利委托给专制的统治者[8]。在霍布斯看来,人是自私自利和贪婪的,人要摆脱自私自利行为只有借助于外部的强制力。斯密显然不同意霍布斯的人性主张,认为自利、自爱与美德并不是对立的,“自我可以追求自利而又不虞堕落为不道德的自私贪婪”,“自惠自利并不必然注定堕落为纯粹的自私”[9]72,因为人内心那个公正无私的旁观者对自我进行省察和监督。斯密进一步指出:旁观者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同情共感,这种情感源自旁观者能够设身处地地考虑当事人的境况和苦恼,想象如同自己处于当事人相似的处境。[10]2122在斯密的观念世界里,人类凭借“公正旁观者”以及与生俱来的同情共感能够形成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生活秩序。他把同情共感融入自我之中,并在《道德情操论》中赋予“自我”新的定义[9]71-72:
当我努力去省察自己的行为……很明显地,我往往要把自我分割成两部分;作为省察者和裁判的我,代表着一种我被审查者和被裁判的我很不相同的性格。前者是旁观者,我努力想进入他关乎我的行为所发出的情感……后者是能动者,那个通常称为我自己的我。
在此,斯密把主体自我分成两半,一半是自己行为的检查者或裁判者,另一半是能动的“我自己”,前者以公正的裁判者的身份控制后者。主体自我中内在的裁决者是最高仲裁人和权威,他能够自动引导我们的品质和行为[3]8586,而无须外在的道德约束力。结果,承载着内心公正裁决者的自我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就不会为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损害别人最小的利益导致自私自利行为。这样就能够使追求自身利益与追求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从而形成一个理性和公义的社会。斯密的人性假设和社会构想为其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亚当·斯密的教育理念
在斯密的理念世界里,文明商业社会中的人是贤明有德、自我克制的。人的德性和智慧成长需要在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中养成。斯密把家庭教育看作是一种天然的教育制度,把公共教育视为一种人为的教育方法[10]287。在道德教育方面,斯密主张青少年必须在家庭教育中养成感恩父母之心、兄弟手足之情和温文尔雅之礼,同时其行为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约束。在教育的总体设计上,斯密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一种是普通民众的教育,另一种是社会富有阶层的教育。
对于普通民众的教育,斯密认为,为了使他们养成社会环境“所需要、所容许的几乎一切的能力和德行”,防止他们堕落或退化,政府须担当教育的责任,并支付必要的教育费用[11]338339。在斯密看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教育,一生全消磨于单纯的、重复性的操作,就没有机会发挥他的智力和才华去探寻解决困难的方法。长此以往,他就失去探究的努力,“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11]339。就普通人而言,他们在从事职业之前都必须接受如诵读、书写、算术、几何和机械学等方面最低限度的教育,并强制他们“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11]341362。普通人所接受的这些知识或原理是“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学的必要入门”,能够为他们日后从事普通职业做好准备。此外,通过接受强迫性的教育,普通人拥有了知识、掌握了科学,一方面能够使人摆脱“无知和大愚钝”、“狂热和迷信”,促进人的智慧和德性成长,另一方面,“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345,人格更高尚。
对于社会富有阶层,斯密主张,他们完全有条件自己解决教育问题,无需政府担负教育费用。因为,在从事“特定的事业、职业或艺业”之前,这些有身份有财产的人有充足的时间,也有足够的财力,来获取那些博得世人尊敬的一切知识。从事某种职业之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像普通人的职业那样单纯,而更多地从事的是极其复杂的脑力职业,况且,他们不是终日忙碌,而是拥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来钻研、掌握各种有用的或作为装饰用的知识。[11]341这样他们就不至于不动脑而流于迟钝,反而更富有理解力和智慧。在道德上,斯密认为,有身份有财产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不得不注意他自身的一切行为。[11]353那些污名失信、有损名望之事,他不敢妄为;社会所要求的高水准的道德,他须努力为之。再者,这些社会富有阶层,拥有丰富知识和科学素养,“科学是对于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消毒剂”,它有助于社会上层人士抵御“狂妄和迷信”的侵扰,从而不至于使社会及普通人“大受其害”[11]354。
斯密的思想体系和教育理念力求基于个体自利原则建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他的观念图像中,新的社会制度不再是由等级、身份构成的层级森严的停滞社会,而是由“习惯、习俗和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异所构成的流动社会[4]83。显然,这种变动不居、流动社会的建构需要人的观念世界不断改造。
三、课室内的实践:学科规训、考试作为观念改造之工具
斯密在其社会构想和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观念改造的工具和教育审查措施。
(一)系统的学科训练
学科是考试、审查的基础。作为修辞学教授,斯密显然明晰学科的价值。从词源学角度,学科(discipline)是一个教育词汇。该辞源自“希腊文的教学辞didasko(教)和拉丁文(di)disco(学)”[9]13。拉丁字根disciplina在古代世界具有双重意义,既指古代文科如哲学及修辞学这一类知识体系、知识修养,也指权力运作如孩童纪律、军纪(disciplina militaris)之类的规约。因此,学科“既要生产及传播最佳知识”,又要“建立一个权力结构”[12],以期控制学习者并使该种知识有效地被内化。在中世纪原型大学,神学、法学和医学等高级学院的教授,运用学科和权威教义或规条对门徒进行严苛的训练,使其掌握某一学科领域的普适方法和真理,遵循既定的学术规范和知识体系。
作为当时英国著名的学术权威,斯密承继原型大学的学科规训方式,对其门徒及慕名而来的求学者进行严格的训练,同时他还接受英国上层贵族之委托,承担教育贵族子弟之重任。从斯密为上层贵族子弟拟定、施行的学习计划中可以洞悉学科规训所承载的价值。斯密在1759年“致谢尔本勋爵”(即佩蒂(William Petty))的信中说道[3]5861:
阁下委托我教育菲茨莫里斯(Fitzmauric)先生之重任,……为了使他在我的直接照顾下,我曾催促他加紧哲学研究。我曾使他通过从正规上说必然是他首先要学习逻辑学课程,使他立刻进入我自己讲授的伦理学。
他每天上一小时逻辑学教授的课,上二个小时我的课,一个小时数学教授的课,一个小时希腊文教授的课,一个小时拉丁文教授的课,除星期六和星期天外,他每天上课六个小时。他从不旷课一小时,早上和晚间到我处复习上边所说的功课成为规矩。
对于他的教育,如果他继续留在此间,我愿意提出一个计划;……下一年里,我将劝他听罗马法教授的讲课;虽然罗马法在英格兰法庭里没有权威,但是学习它是为学习英国法做良好准备。
在他去罗马法教授讲座听讲的同时,我将亲自与他一起阅读封建法的基本原理,它是当前所有欧洲国家法律和政府的基础。
从斯密所列的学科内容看,逻辑学课程包括语法、修辞、文学等,斯密主讲的道德哲学课涵盖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1]51,数学课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光学等,古典语言包括科学、哲学和神学研究所必须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些学科内容涵盖十分广博的知识领域。从斯密所安排的学科课程次序看,先学习哪些课程、后学习哪些课程、为什么学习这些课程等,都是严格遵循学科逻辑顺序,依照学习者的实际情况而设计。在这种系统而严苛的学科规训下,如果学习者能够把学科知识内容内化,他就能够遵守学术规范,掌握知识体系,明晰道德准则,理解客观事物及人类社会,从而形成对事物和人的正确概念。这种规训最终能够让学习者拥有道德和纪律,具备自主自持(selfmastery)的品质。
(二)日常化教学测试
与其前辈的教学不同,斯密突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主张学生的竞争与合作,并把授课内容的考核日常化。据记载,在格拉斯哥大学日常教学中,“斯密天不亮就开始工作,早上七点半至八点半给普通班上课。接着,在上午十一时就早上的讲课的内容进行一小时的测验”[1]48。这种新的教学程序和教学考核方法是斯密的前辈所不曾使用的,因此,斯密成为“格拉斯哥大学首创的一种以考试为基础的学习方法的先行者”[13]。据后来承继其课室教学方法的贾丁(Geoge Janline)教授记载,斯密讲课时的情景[9]70:
经常把学生归入团结在一起的组别,在组内各人相互扶持,分担感受(“同情共感”的团伙动力)的意识,与每个人追求脱颖而出的欲望(个人追求“比试”的策动力)相互结合。
在学习动力的推助下,学生做笔记、提问和写作,最后以“即席考试”、教师评分等方式审查学生的学习成效。或许大学课室的教学实践激发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宏观构想,如果按照他的教学法世界的意象来构建经济世界,那么就意味着其理论构想能够在课室的微观经济学中应用,自然也可以在自由市场的宏观经济学中实施[9]7273。从术语的使用上,斯密课室场域中的“比试”、“同情共感”,与其著作《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中的“竞争”、“同情共感”一脉相承,并分别代表了促进个体和社会不断进步的推动力。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竞争”、“同情共感”成为贯穿斯密的伦理学、经济学和教育学思想的“铰链”。
(三)国家层面的入职考核
就接受基础教育的普通人而言,斯密主张,一方面国家要奖励或奖赏那些学业优良的儿童,另一方面普通人在就业或谋职之前都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检定”,以利于国家实施强制性的全民基本教育。[11]342343针对那些中等乃至中等以上的富有阶层,斯密主张国家须要求他们几乎全部从事科学及哲学的研究,并设立较高深、较困难的科学检定或考试制度,无论何人,他在从事某种自由职业或获取某种名誉之前,都必须经过这检定或考试。[11]354斯密把考试提升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并作为强制性规约,由是彰显国家权力对某些知识形式或教育形态的掌控力量。
(四)测试考核之效用
斯密所实施的测试考核对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首先,考试激发人的活力。斯密“亲身显示了考试/审查(这种形式)对他自己所发挥的力量”,“以此向学生提倡他的重要新思想”。正如受到斯密重要影响并成为斯密得意门生的贾丁所言,考试/审查作为以前未曾用过的方法,一旦使用就使人的潜在力量“从沉睡中苏醒,变得生气勃勃”[9]75。在考核的激励之下,学习者处于竞争、奋发努力的场域之中。但是,这种竞争并不是无序和自私自利的,它受到人本性中内在道德的规约。如果说考试能够激发个人充分而合理的自由竞争意识和创造力,以谋求自我发展和个人利益,那么在竞争的同时每个人还必须兼顾他人,存有同情心,保持其行为的合宜性,以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从而最终将个人的自我行为导向社会共同善。这也许是斯密在教室中创制考试和竞争的本意所在。
其次,考试/审查形构“理性”的人。从日常教学程序和对学习者所拟定的学习计划看,斯密对自己的授课进程、考试时间以及学习者学习内容、时间的安排,都经过精心设计和精细核算。这一方面能够审视、评核学习者的学习表现及其进展,促使其不断努力和自我修正,另一方面这种算计、考核也在审查教育者自身,促使其反省自身不足,提升其学识水平和教学能力,最终使教学双方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从主体的发展变化看,讲课后施行测试、评分促使教学双方都面对经常性的监视和评判,激发其自我反省自觉,从而摆脱他人或外在的监督和评判,学会对自身的思想、行为作出经常性的审查,生成、建构自我审查的主体。[14]在教学实践中,斯密也正是通过自我审查、自我规训提升教学效益,达致教学完美。比如,在讲课过程中,斯密比其他教授更加关注听课者的反应,即使学生的一个细微动作或表情,斯密就能够察觉、判断自己讲课的效果,如果发现讲课存有瑕疵或不足就立即“改变题目和讲课方式”[1]53。这种自我审查和自我规训有助于培育人谨慎的美德。谨慎的美德促进理性的达成和个人幸福的获得。此外,斯密还从仁慈和对别人幸福的立场,提出人所必须拥有的严格的正义和合宜性仁慈的美德。无论人的明智、审慎还是正义、仁慈,在斯密看来,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维持的,而人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源自人内心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他是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裁决者”。[10]293在斯密的理念世界里,教育及其规训有助于形塑人内心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在“公正的旁观者”的主导下,人的理智和美德必然趋向尽善尽美,在各种可能的环境和情形中达致最合宜的行为习惯。
四、结语
从斯密所处的时代起,课室的创立及其运用渐进成为新型的教育场所,课堂中的学科训练、考试也成为现代教育规训方式,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推广。这种教育形态改造着不同的知识形式和教育实践样态,同时也形构人的观念世界。在教育规训制度下,课室中的学科训练、考试或自我审查能够使人发现自身弱点,认识自身不足,在自我批判、自我反思中改造其灵魂、思想和行为操守,得到智慧、纯净和完美。在理性和效率操控下的现代社会,课室已不局限于狭小的空间,学科训练、考试也不限定于窄小的课堂,课室形态和考试审查方式已打破有限的界域,扩延至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社会控制方式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人不过是在监控情形下把一些知识内化了的主体,抑或是由知识、权力和组织客体化了的“臣属主体”。人在被规训或自我规训中改造其思想和行为,这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
参考文献
[1]雷,J. 亚当·斯密传[M].胡企林,陈应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拉斯达尔,H.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M].崔延强,邓磊,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16.
[3]莫斯纳,O.,罗斯,E. 亚当·斯密通讯集[M]. 林国夫,王翼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David,H. Towards a Theory of Schooling[M]. London: Falmer Press,1989.
[5]Seaborne,M. The English School: Its Architecture and Organization 1370-1870[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1971:268.
[6]Gibson,J. The History of Glasgow[M].Glasgow:Oliver & Boyad,1777:143.
[7]Wilderspin,S. On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ng the Infant Children of the Poor[M].London:Westley and Davis, 1823:18-26.
[8]霍布斯,T. 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4.
[9]华勒斯坦,I.,等.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0]斯密,A. 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钦北愚,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1]斯密,A.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2]Hoskin,K.W. Knowledge: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ies in Disciplinarity[M].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93: 301-304.
[13]David,H. Adam Smith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Classroom[J].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1980(12):281-298.
[14]Hoskin,K., & Macve,R. Accounting and the Examination: A Genealogy of Disciplinary Power[J].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1986(11): 105-136.
本文由校风云培训学校管理系统责任编辑,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感谢您的支持!